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在回忆中时刻能找回自己
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在回忆中时刻能找回自己
2017年05月18日 10:53:41 浏览量: 来源:中国搜索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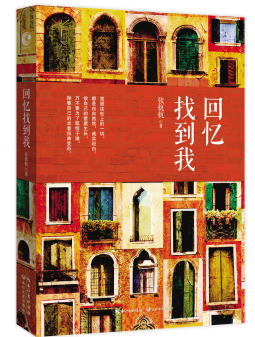
《回忆找到我》
“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
“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
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至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时能时时找回自己。
张抗抗用她独有的笔触书写了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母亲病重身子压住了时间、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友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面对周遭的情与事,张抗抗表述出了真心感悟。
著名作家汪兆骞这样评价张抗抗的新书《回忆找到我》:“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阔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了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为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
苏醒中的母亲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年近80岁高龄的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而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我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大脑表层的淤血,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以及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突然一扇一扇地敞开。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我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停用后的第二天夜晚。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妈妈会说话了,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第二天清晨我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妈妈床边,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妈妈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奇怪地冒出了许多不连贯的文言文。那几天我们差点儿以为母亲从此要改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古文,以便与母亲对话。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
如今再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她有过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那天,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却十分艰难缓慢。她明明是醒过来了,但我时常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她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丝丝缕缕不见踪迹;有时她又好似深深潜入了水底,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妈妈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一如冷傲的秋菊,在凋谢前仪态万方地告别演出。
母亲一生待人和气宽容,对于生活的种种磨难,她从来没有抱怨没有忌恨:即便遭受如此大难,她依旧坦然承受着病痛,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乐观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坚韧仁慈的母亲而骄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中那种本真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从健康的青年时代直到病前的老年岁月,曾经给予我的教诲与爱,都在她意识蒙眬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一个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自我意识尚不能受制于理性控制的时刻,她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思维和行为,应是她心中最坚实的内核与底蕴。
节选自《回忆找到我》
责任编辑:张东红 [网站纠错]相关阅读
- 2017-03-30《我的小小忧伤》用同理心疗愈“小小忧伤”
- 2017-03-25春风三月,和夏烈、石一枫赴一场樱花文会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