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读书乐》: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
《四时读书乐》: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
2016年12月06日 14:58:03 浏览量: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王稼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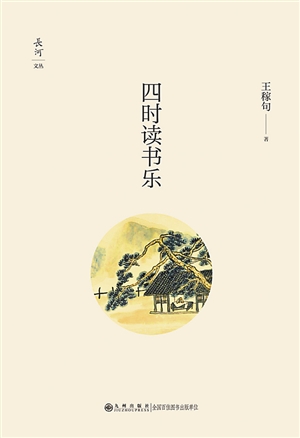
《四时读书乐》
王稼句 著
九州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这个书名,乃取集中一篇的题目,那是借着苏州某旧宅的砖雕门楼说事,因在那门楼下枋上雕镂着“四时读书乐”的场景。宋末元初仙居人翁森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歌》,四首七律,分春夏秋冬,咏读书之乐。这四首诗传播广泛,很多人都抄写过,碑帖流传是不少的,过去在坊间,时常能见到赵孟頫、文徵明、梁同书、成亲王永瑆、钱泳、林则徐、李鸿章、黄自元、孔祥珂等人的印本,尤其是徐郙、陆润庠、曹鸿勋、张謇四位状元,更写得温雅圆和、骨韵兼善,堪称台阁体的典范。这些碑帖,向来有很好的销路,由于那四首诗本身写得不错,像“绿满窗前草不除”“数点梅花天地心”等,都算得上名句,抄它们的人几乎都有大名,且大都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这对孩儿们来说,那就不但是理想的临摹范本,名人效应更成为人生楷模,而诗中描绘的读书境地,也让他们潜移默化,诗境与心境融合了,四时读书,也就有了四时不同之乐。正因为如此,这组诗不但有碑帖,在笔筒、墨盒、搁臂、水盂、镇纸等文具上也很常见。画人则将它们作为一个题材,大都依诗意作四屏条。至于砖雕则不多见,故那门楼上的故事,题材不谐俗,寓意不庸浅,创造了一个让人神往的读书境界,作为民居建筑装饰,算是上乘的。
读书既有年龄之分,更有性质之别。孩儿入塾启蒙,戒尺和罚跪,限制了他们自由的天性,哪有什么读书之乐?冯梦龙《广笑府》就记了一首《懒学诗》,咏道:“春游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凄凉无兴趣,不如耍笑过残年。”仇英《摹天籁阁宋人画册》中一帧“村童闹学”,晚清天津杨柳青年画《闹学顽戏图》,就反映了孩儿们摆脱束缚后的快乐心情。到了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的各个时段,那“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映雪囊萤”“然荻读书”诸多故事,又何乐之有?尤侗《艮斋杂说》卷五记了一则轶话,说是某君将死,对亲友说:“吾死无所苦,所苦此去重抱书包上学堂耳。”那诙谐中是含着悲哀的。且不说科举时代,民国了,上学读书,依然负担沉重,知堂在《苦竹杂记·谈中小学》里说:“一天八点十点的功课,晚上做各种宿题几十道,写大字几张小字几百,抄读本,作日记,我也背不清楚,各科先生都认定自己的功课最重要,也不管小孩是几岁,身体如何,晚上要睡几个钟头,睡前有若干刻钟可以做多少事。”时到如今,变本加厉,为升学,为高考,为考研,读书之乐更无从谈起。更有论文一道坎,又少不了要去读书,挖空心思,这里抄一点,那里偷一点,拼拼凑凑,应付导师,岂不知导师也是这样过来的,真是苦不堪言,然而不堪言者,更胜过那苦,还会有什么乐。
然而读书固然有乐的,所谓乐,也就是满足自己的阅读愿望。依我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强迫的要求,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求自己的喜欢,那读书就有意思,有佳境,有乐趣了。犹记初读小学,散学后走过几条小巷,到一家小书摊,搬一张小凳,一分钱一本,看得真是津津有味,这是我早年所得的读书之乐。我在上大学前的学生时代,几乎都给“文革”占了,上课都不正常,更没有什么作业,就千方百计去找闲书来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50多年来,正经书没读过几本,闲书却读了不少,至今一无所成,原因大概也在于此。但我却并无“老大徒伤悲”的遗憾,似乎这样也挺好,故至今还是在杂览,有什么读什么,想读什么读什么。读《启颜录》,读《笑林广记》,不时会舒眉破颜,甚至笑出声音来;读《古拉格群岛》,读《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心情沉重,然而那些往事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大暑后这几天,异乎寻常的炎热,不想做事,也做不出什么事来,午前就泡一杯酽冽的祁红,找出一本《苦口甘口》,躺在藤榻上随便翻翻。翻到一篇《灯下读书论》,知堂说:“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这几句话,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完全的意思,我的读书,也无非是想多知道一点世上的事。
(本文为《四时读书乐》题记)
责任编辑:张东红 [网站纠错]相关阅读
- 2016-12-01碎片化快节奏的信息时代 如何做一个靠谱...
- 2016-11-26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
- 2016-11-23古渊头:耕读传家文脉深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