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2016年11月26日 13:46:09 浏览量: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雪瑛
王:面对那些“回避现实”的疑问,你写了99篇文章,23万字,让大家感受到了你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山里人的日子。你当时开始动笔的时候有整体构想吗?
韩:没有。很多章节不过是日记,后来稍加剪裁,有了这一本。当然,我从不认为这里就是现实的全部,但这种现场感受至少是现实的一部分,比某些名流显贵那里的“现实”更重要,比某些流行媒体东抄西抄嚼来嚼去的二手“现实”可能更可靠。中国一大半国土是乡村,至少一半人口是村民,这些明明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被排除在“现实”之外?
王:《山南水北》是你对思想和理念的一种感性的实践和体悟,是你个人对现代化的一种自由选择,一种个性化的文学表达。从此书出版至今9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山南水北》对你的意义?
韩:怀疑和批判永远都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必须成天活得怒气冲冲,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思想文化而言,18世纪以来不论左派右派都是造反成癖,反倒最后是易破难立,有破无立,遍地废墟,人们生活中的自杀、毒品、犯罪、精神病却频频高发,价值虚无主义困扰全世界。文学需要杀伤力,也得有建设性,而且批判的动力来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是对美好的信仰,对美好一砖一瓦的建设。缺了这一条,缺了这一种温暖的思想底色,事情就不过是以暴易暴。用廉价的骂倒一切来给自己减压,好像别人都坏透了顶,那么自己学坏也就有了理由。这是一种明骂暗赞的隐秘心理。《日夜书》里有一句话:“最大的战胜是不像对方,是与对方不一样。”就是针对这一点说的。
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呈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韩:就文化演进而言,趋同化和趋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全球化不过是这两个轮子的古老故事,从村庄级上升为全球级,单元边界扩大而已。人都要吃饭,这是普适性。但什么饭好吃,人们的不同的口味受制于各种条件和相关历史,就有了多样性,其中包括民族性。我曾经以为舞蹈是最不需要翻译的,最普适性的,后来才知道肢体语言也有深刻的族群差异,我的语汇你可能无感,你的语法我可能不懂。舞蹈尚且如此,运用民族文字的文学怎么可能完全“一体化”?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如果有的话,肯定是趋同化与趋异化在更高层面上重新交织,决不是拉平扯齐、越长越相像。否则,那个同质化世界一定乏味透顶,失去成长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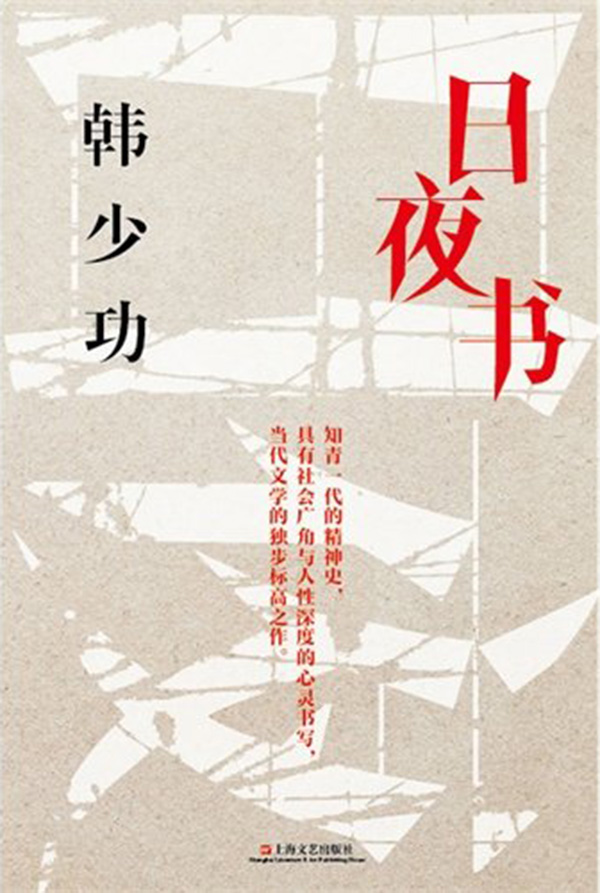
《日夜书》 韩少功著
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东西
王:《日夜书》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这是你的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描摹知青这一代,来审视和思索自己的人生。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
韩:有些书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志在卓越。有些书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意在解脱和释放。《日夜书》大概属于后一种。这本书写作耗时一年多,触动了一些亲历性感受,算是自己写得最有痛感的一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淡出历史。我对他们——或者说我们——充满同情,但不想牵就某种自恋倾向,夸张地去秀苦情,或者秀豪情。我把他们放在后续历史中来检验,这样他们的长和短才展现得更清晰。由这一代人承重的时代,为何一面是生龙活虎而另一面是危机频现,才有了一个可靠的解释线索。“中国故事”难讲,最难讲的一层在于人和人性。没有这一层,上面的故事就是空中楼阁。“苦情”和“豪情”宣示虽不无现实依据,但容易把事情简单化,比如把板子统统打向别人,遮挡了自我审视。我的意思是,每一代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恋,但我希望这一代人比自恋做得更多。
王:我觉得《日夜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摆脱了自恋,也摆脱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套路,而是真正地以小说的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回望和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回避卑微,不回避平淡,不回避内心的纠结。
韩:郭又军是个仁义大哥,但他曾经把“大锅饭”吃得很香,结果误了自己。贺亦民在技术上是个超强大脑,但他对社会不无智障,江湖化的风格一再惹下麻烦。马涛有忧国忧民的精英大志,但从自恋通向自闭,最后只能靠受迫害幻想症来维持自信……他们该不该把这一切的责任推给社会?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人性弱点,他们的奋争是否才会更真实、更艰难、也更让人感叹?相关的历史描述是否才更值得信任?
王:你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中,你似乎收敛了思想的锋芒,而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带出往日的一段段经历,那些物质贫乏,精神亢奋的日子,同样通过人物来连接往日与今日之间那巨大的沟壑,在往日和今日,现实与记忆中塑造出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勾勒出人物在时代的风云起伏变幻中形成的命运,而不是想做什么定义和结论。
韩:写人物,当然是小说的硬道理。我们可能已经记不清楚《水浒传》或《红楼梦》里的很多具体情节,但那些鲜活人物忘不了,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一点东西。《日夜书》是留给自己的一个备忘录。写谁和不写谁,重点写什么,肯定受制于作者的思想剪裁,但我尽量写出欧洲批评家们说的“圆整人物”,即多面体的人物,避免标签化。有人说,这会不会造成一种价值判断的模糊?问题是,如果只有面对一堆标签才有判断能力,才不会模糊,那也太弱智了。
责任编辑:林庭宇 [网站纠错]相关阅读
- 2016-11-24严歌苓:更乐于看到小说角色“出逃”
- 2016-11-21话剧《白鹿原》:在时代动荡中洞见恒常
- 2016-11-21简论《大高原》的审美价值
- 2016-11-21文学与科学,距离有多远
- 2016-11-21贾樟柯:艺术离不开人间烟火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