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2016年11月26日 13:46:09 浏览量: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雪瑛
【编者按】本文系文学评论家王雪瑛在今年对作家韩少功的一个长篇访谈,因篇幅原因,澎湃新闻刊登其中的部分章节。在访谈中,作家韩少功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的写作,从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创作,回顾了自己的知青生涯到现在“山南水北”的乡村生活,也对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和当下思潮、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评价。
在访谈中,韩少功认为,“80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90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在他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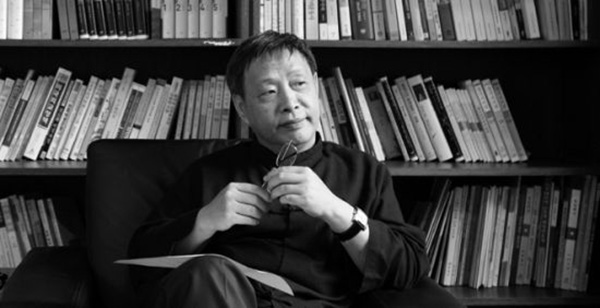
韩少功
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盲区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你不仅以小说的形式拓展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空间,同时以散文的形式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前沿。这是你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慎重的选择?
韩:这样说吧,小说是一种“近观”方式,散文则相当于“远望”。这种“远望”比较方便处理一些散点化、大广角的材料,即不方便动用显微镜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看黄山就不一定合适吧?在另一方面,在文学与理论之间,有一个叫做文化随笔和思想随笔的结合部,方便一个人直接表达思考。我曾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心智成熟经常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肌肉扩张,有一种大娃娃现象。很多问题来得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等不起长效药,就得用速效药。思想随笔有时就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工具,好不好先用上再说。
王:你的散文写作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小说与散文不光是两种体裁,而且常常承载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说的虚构是一条,是否直接表达思想也是一条。此外可能还有其它,比如慎于判断和勇于判断的态度差异。一般来说,小说模拟生活原态,尊重生活的多义性,作者的价值判断经常是悬置的,至少是隐蔽的。比如安娜·卡列琳娜怎么样,林黛玉或薛宝钗怎么样,由读者去见仁见智好了,作者最好站远一点,给读者留下自由判断的空间。但散文不一样,特别是思想随笔需要明晰,有逻辑和知识的强大力量。伏尔泰、鲁迅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模糊。在这里,模糊和明晰,自疑和自信,是人类认识前进所需要的两条腿。但两种态度有时候脑子里打架,怎么办?我的体会是要善于“换频道”,把相互的干扰最小化。一旦进入这个频道,就要把那个频道统统忘掉,决不留恋。
王:在《进步的回退》中,你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了你的一部重要的充满感性的散文长卷《山南水北》。

《山南水北》 韩少功著
韩:以前恋爱靠唱山歌,现在恋爱可能传视频。以前杀人用石头,现在杀人可能用无人机……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变化,但变中有不变,我们不必被“现代”“后现代”一类说法弄得手忙脚乱,好像哪趟车没赶上就完蛋了。事实上,经济和技术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就道德和智慧而言,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牛皮可吹。这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常有的盲区,恰好也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在《山南水北》中,你以生动质朴的语言记叙了你的乡村生活。你怎么看待自己现在的乡村生活经验?
韩:我在那时已住过十六个半年。最初只是想躲开都市里的一些应酬、会议、垃圾信息,后来意外发现也有亲近自然、了解底层的好处。说实话,眼下文坛氛围不是很健康的,特别是一个利益化、封闭化的文坛江湖更是这样。总是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泡,你说的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
相反,圈子外的农民、生意人、基层干部倒可以让你知道更多新鲜事。这里的个人原因是,我从来就有点“宅”,不太喜欢热闹,经常想起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每当我从人多的地方回来,就觉得自己大不如以前了。
责任编辑:林庭宇 [网站纠错]相关阅读
- 2016-11-24严歌苓:更乐于看到小说角色“出逃”
- 2016-11-21话剧《白鹿原》:在时代动荡中洞见恒常
- 2016-11-21简论《大高原》的审美价值
- 2016-11-21文学与科学,距离有多远
- 2016-11-21贾樟柯:艺术离不开人间烟火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