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那些浙江人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那些浙江人
2017年01月19日 09:17:19 浏览量: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李月红
15世纪初的爪哇,是由一个大王国满者伯夷以及几个小港口所统治。
中国的船只为了跟爪哇北部沿岸的地方势力打交道,也因此得中途停留多次。一般而言,马欢在这些港口都会遇到三类人:穆斯林(阿拉伯人与当地改信者)、汉人,以及当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他一如往常,观察着几个港口城镇平常的生活方式: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箸。男妇以槟榔荖叶聚蜊灰不绝口。
马欢在爪哇看到有人用“人物鸟兽鹰虫”的纸画来进行表演。他感觉这些画像“如手卷样”。表演进行时,那人会对着听众展开部分卷轴,开始讲故事。“众人圜坐而听之,或笑或哭,便如说平话一般。”24 卷轴画表演遍布于当时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马欢观察入微,近距离辨识出这种表演的常见模式。卷轴画表演常见于孟加拉、拉贾斯坦(Rajasthan)、波斯、东南亚,还有中国。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才意识到这种大众娱乐的共同特色。
除了对气候、动植物、风俗与贸易商品的惯常叙述以外,马欢还注意到泰国的寺院传统与中国的相当类似:“国人为僧为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往庵观,持斋受戒。”
船队从阿瑜陀耶出发,再次沿马来半岛而下,前往今日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港。马六甲约建于1375年至1400年间(只比马欢第一次的出行早了一代人的时间),是东南亚西部地区口岸中的冉冉新星,也是印度洋与东南亚水路之间的主要转运站。马欢记载:马六甲过去名义上是由泰国掌控,但当地头目力求独立,先前下西洋的船队便用“双台银印冠带袍服”认可了头目的独立地位。船队领袖在马六甲建碑封域,头目随后也赴京面圣。
但到了第四次下西洋时,马六甲国王正对受制于中国而心怀不满。根据马欢所述,国王新改信了伊斯兰教,穿着就像个阿拉伯人。他“以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衣,其样如袍,脚穿皮鞋”。马欢将国王采用这种服饰的做法,与其改信伊斯兰的记载并列在一块儿,这很有意思。不过在第四次下西洋时,马六甲国王和中国的朝贡关系仍然密切。马欢提到船队在马六甲多待了一段时日。船员将贡品与他们搜罗而来的贸易货物卸下船,放进安全的营寨,等之后一行人从印度洋回来再来上货。明帝国舰队通常会在马六甲分头前进,一部分航向孟加拉,其他船只则前往非洲或印度西海岸。公元1413年,马欢这一部分的船只穿过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之间,往西北航行,在两个港口停留。小国的重要性不高,马欢干脆用寥寥数笔描述,“土无出产,乃小国也”。
马来半岛上开采锡矿的情景倒是吸引了马欢的注意力。锡在15世纪时还是个重要贸易项目,重要的程度一如10世纪印坦沉船的时代。
“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令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
每一块锡都有标准的重量,绑成一大把,每把有四十块。潜水员打捞10世纪印坦沉船时找到的正是这种块状的锡。
苏门答腊岛之行一结束,船队便调头往西,经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前去斯里兰卡。虽然明朝舰队拥有超过两万名士兵,马欢这边的分舰队可能也有为数六千人的部队,但他从未记录有战斗发生。船队从来没有攻击或破坏任何口岸。
若要估量贡物,就得将当地的钱币与度量衡换算成中国的标准。这在马欢的回忆录里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斯里兰卡,国王“以金为钱,通行使用,每钱一箇,重官秤一分六厘”。船队接着从斯里兰卡继续往西,绕过印度南端,往马拉巴尔而去。
马欢清楚地意识到这片植物茂密、满是椰子树的海岸,是个盛产胡椒的国度。
“土无他产,只出胡椒,人多置园圃种椒为产业。每年椒熟,本处自有收椒大户收买,置仓盛贮,待各处番商来买。”
到了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马欢则是第一次出洋),中国似乎已经与几个重要港口当地的国王建立了关系。船队的上首外交官先是致赠袍服与诏书,表示尊敬,接着双方代表才开始谈生意。国王的代表与船队的领船大人首先验明中国丝绸与其他货物的成色,然后议择某日打价。日子一到,“众手相拿”,同意“或贵或贱,再不悔改”。城里的商人接着把“宝石珍珠珊瑚等物”带来。议价之事“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船队随后的所有交易,都要根据这些定好的价格进行。虽然明朝舰队武力强大,但长达数月的谈判过程,暗示了明朝不单是用命令的方式在指定价格与交易条件。
这种大规模的议价并非当时马拉巴尔的海港的常态。商人就只是买进他们付得起的货,价格则是由市场决定。后来在回忆录里,马欢也描述了卡利卡特平时的交易状况。
“各处番船到彼,国王亦差头目并写字人等眼同而卖,就取税钱纳官。”
中国朝廷有着要长期经营的宏图大计。郑和在好几个港口立了石碑,上面的声明都表示了朝廷的意思,写着:“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像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这种当地国王,哪儿能够从与中国的关系里得到什么?可是,当一支有好几千名明朝士兵的军队出现在自家港口时,他可能也没什么选择。但他还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明朝答应支持他对抗家族里的对手以及外敌。只是这种承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毕竟这支舰队每几年才造访一次。而明朝部队真去捉拿东南亚当地的逆党、让国王重登宝座的事情,马欢只记载过一回。
马欢有一次抓住机会,从卡利卡特(可能是在漫长的谈判期间)单独前往麦加—或许是搭当地的船只去的。这座圣城深深感动了他。他写了许多我们料想得到的题材:建筑、当地的瓜果蔬菜,以及贸易商品。“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
霍尔木兹是第四次下西洋行程的最西端。马欢在那儿看到一种街头表演,让他目不转睛。
“(表演者)令一闲人,将巾帕重重折叠,紧缚其猴两眼,别令一人潜打猴头一下,深深避之。后解其帕,令寻打头之人,猴于千百人中径取原人而出,甚为怪也。”
船队迅速从霍尔木兹沿原路绕过印度回到马六甲,装载留交当地保管的商品,然后走最短的航线返回中国南方海岸。公元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的舰队回到中国。1421年时,马欢参加了他第二次的西洋之行,等到他返国时,官场中强大的士人团体正与宫中支持下西洋的宦官对垒。公元1431年时还有一回,马欢也再度登船,担任阿拉伯语通译。到了15世纪40年代,明朝皇帝下诏焚毁下西洋的所有记录。只有少数回忆录、几张海图与一张地图幸免于难。另一份诏书则下令停止对外贸易,甚至命沿海居民迁往内陆。
不过,对马欢来说,这两趟旅程的意义却与此完全不同。他就像伊本·法德兰、伊本·巴图塔、玄奘等许许多多的旅人,在陌生的信仰与风俗中探寻模式与结构。他分析自己的见闻与体验,试着让人了解这一切。他拿东南亚的娱乐与中国能找到的种类相提并论,称许多地方的人“整洁”、勤奋发展当地的生产。他们的饮食虽然不同,但饶有趣味。到了中东的港口,人们也因为马欢是个穆斯林而接纳他,尤其是在麦加—这让他铭感五内。
许多年后,马欢一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为这部回忆录写了篇简短的后序,希望在马欢努力找官场中人赞助、将本书付梓出版。
后序提到马欢事竣归乡里,说他这个人“恒出此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异域之事”。马欢的回忆录里充满着他对于能够去见识、了解中国以外的人群如何生活、嫁娶与实践这么多信仰,心里有多么感激。而他所体验的一切也深深地改变了他,感动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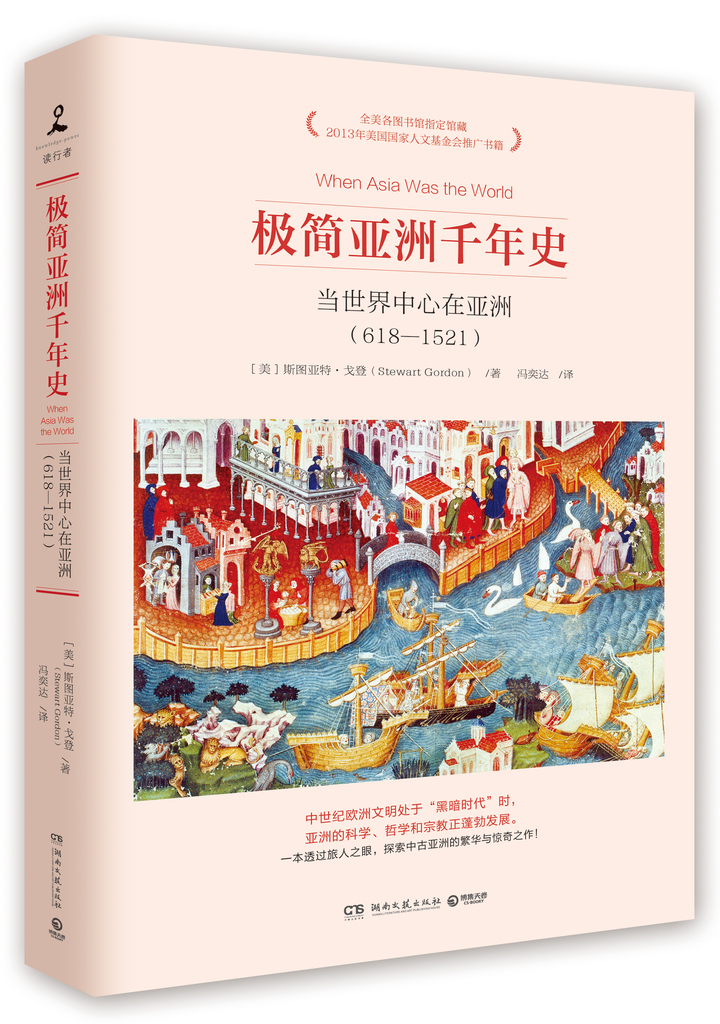
新书书封
由密歇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获得者斯图亚特·戈登耗时6年写就的《极简亚洲千年史》一书,2016年12月出版上市。在这本著作中,斯图亚特通过细腻的描绘与大量原创研究,向读者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历史真相:当欧洲深陷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时,同时期的中古亚洲则正处于最辉煌的巅峰,在那漫漫千年中,亚洲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在6年时间里,斯图亚特阅读超过50本回忆录,重构5次,撰写了13份草稿,终将这本书写就,被列为全美图书馆指定馆藏。
文化的多样性随着交流日趋交融,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的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重新翻涌起时代的潮流,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组织的推动下,亚洲各国从经济、文化延展到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势必将再次让世人侧目。
正如作者斯图亚特所说:“一个国家会扩张、会收缩,有起也有落,但许多跨越宗教、族群认同与语言的纽带却始终不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流网络、相互尊重与共同智慧,是我们能留给未来几代人最重要的遗产——而这种想法,或许就是能从本书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责任编辑:林庭宇 [网站纠错]相关阅读
- 2017-01-11《极简亚洲千年史》一滴水折射历史的耀...
- 2017-01-10丝路旅人的历史记忆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