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 包括天气
历史写作大师巴巴拉·塔奇曼
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 包括天气
2016年12月05日 15:55:33 浏览量: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谭宇宏

巴巴拉·塔奇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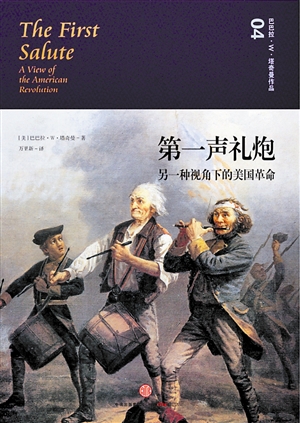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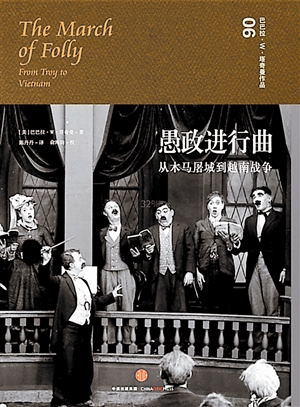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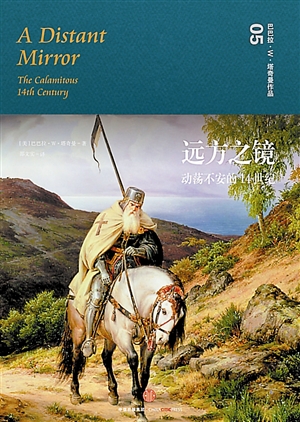
“历史比小说更精彩”,读过历史写作大师巴巴拉·塔奇曼的书后,你会相信确实如此。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两部获奖作品《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畅销不衰,写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且常年背着家庭妇女的本职,塔奇曼是个传奇。
中信出版社首次集结出版了六部巴巴拉·塔奇曼作品——题材涉及特洛伊的陷落、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越南战争。题材广阔,文笔闪耀,读来令人击掌,又不乏警醒作用。
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美国老太太生于1912年,卒于1989年。虽然她的获奖作品被归类为非虚构文学,但她明白表示,讨厌“非虚构”一词,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也因此被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誉为“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
出身世家 眼界高远
一开始巴巴拉·塔奇曼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中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老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外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时候,塔奇曼的兴趣是历史和文学。1933年毕业时,她开始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工作。该学会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当时学会的国际秘书长威廉·L·霍兰被派去日本东京指导《太平洋经济手册》的编纂工作,塔奇曼则在1934年的10月成为他的助手。她在东京待了一年,然后在北京暂住了一个月。暂居日本的一年中,塔奇曼为学会的出版物《远东调查》和《太平洋事务》写了一些文章,尽管主题都不太热门,但她的文章依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回到纽约后,塔奇曼在1936年开始为《国家》杂志工作,她的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曾经是该杂志的受托人。受《国家》委派,她在1937年至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之后,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博士结婚。珍珠港事件之后,塔奇曼的丈夫加入了美军医疗队,塔奇曼和女儿跟随丈夫到了亚拉巴马州的拉克营,当他于1943年和医疗队远渡重洋时,塔奇曼和女儿回到纽约,并开始为战时新闻局工作。
如此出色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使塔奇曼往外交或行政工作方向发展,但她志不在此。1956年,塔奇曼重拾早年兴趣,出版了《圣经与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这是一本从古代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从那以后,塔奇曼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面向大众写作历史。
题材广阔 非常好读
塔奇曼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她讲的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她主张把历史看作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独特性。
同时,塔奇曼也非常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历史作家写过去的事,但他们不是过去的人,因此他们只能无限接近历史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用证据说话”。《八月炮火》出版后,有一个读者告诉塔奇曼,他尤其喜欢《八月炮火》中那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位读者以为这是塔奇曼艺术加工出了一种末世景象,但事实上那是真的。这个细节来自一个英国军官的回忆,这位军官参加了登陆,听到了雷声,看到了血色的日落,因此塔奇曼把这段描述写进了书中,“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塔奇曼如是说。
塔奇曼笔下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也许费正清的评价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个事例也可以说明塔奇曼的历史写作风格,她曾经在《历史的技艺》中谈及历史写作在于发现“新东西”。这里的“新东西”并不是为了有意颠覆前人所见而存在的。新东西,可以是一个未被重视的人,一件被忽略的事件,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是“计以盎司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法国社会主义史,导师要他了解19世纪某年法国普通商品的物价,对塔奇曼来说,这一点都不值得惊讶,掰开揉碎是每个研究历史的人的基本功,而她,一个一辈子都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比科班历史学家更强的地方,是她能够将“盎司”揉入到“史识”之中。
责任编辑:张东红 [网站纠错]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1662号